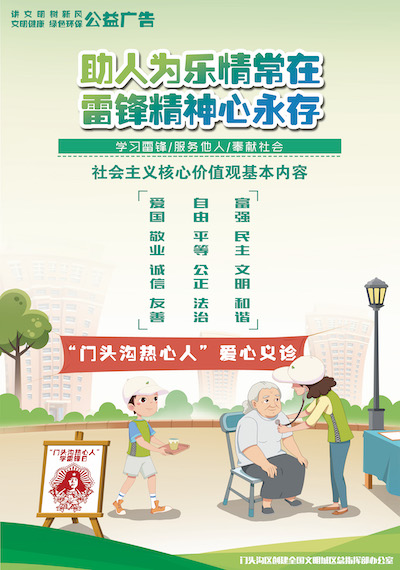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是古代农耕文化对自然节令的反映。晋陶渊明曰:“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说的是仲春时节春雨应时而降,春雷开始震响。潜藏的虫类受到惊动,草木也纵横滋生舒展了。实际上,春雷惊百虫,百虫得复苏的情景,主要指的是南方,北方此时尚冷,故而惊蛰并无惊虫也。山河大地经历了早春的懵懂,春意日渐浓郁。春雨过后,一切清新如洗,行走在乡间,人们会感到连空气都带着诗情画意。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倚门而望,我便问她在看什么,她说:“春天来了,虫儿们睡醒了,燕子也就快回来了。”我随着母亲的目光,看到了屋檐下发旧的燕巢,知道她之所以愁怅,不过是在盼望着燕子归来罢了。母亲说:“咱北方山区,节气比南方要晚上个把月,等燕子飞回来的时候,咱庄户人也该打理田地,忙着耕种了。”后来,我渐渐懂了,春天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燕子归巢于此时,预示着新一年的开始和在机遇中收获希望。
燕子,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益鸟。它身着多色,头顶、颈背部至尾上覆羽,带有金属光泽的深蓝黑色,翼为黑色,飞羽狭长。其颏、喉、上胸棕栗色,下胸、腹部及尾下覆羽浅灰白色,无斑纹。其尾叉形,蓝黑色,喙黑褐色,短小而龇阔。“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在诗人心中,燕子是春天的情人,在村人眼里,它则是吉祥鸟,是能知吉凶祸福的精灵。村里人常说:“燕子来家做个窝,家中喜事多又多。”
燕子的确喜欢栖息于人类居住的环境,与人类久处而和谐。我们从小的时候,老人就告诫说:“不能伤害燕子,否则就会遭到天谴。”此告诫代代相传,几乎是不成文的规矩。燕子似乎知道人们不会伤害它,因此不但不怕人,反而喜欢在农家堂前做窝筑巢。但是,燕子对筑巢的选择却并不随意,它们喜欢安静和谐的环境,不喜烦躁人家,更不愿进恶人门,如果谁家会被它们选中,说明这个家庭氛围一定和谐融洽。倘若遇到整天吵闹的烦心人家,它们非但不去,而且会避而远之。
每年仲春过后,万物复苏,冰河畅流,大地旷野桃红柳绿,一群群的燕子,犹如黑色的闪电,羽翼上闪耀着绸缎般的光芒,飞进山村的农家院落。此时,家乡人仿佛见到了阔别的老友,脸上绽露出久违的笑意。燕子造窝,大多由雌性建造,一旦求偶成功,雌雄燕子便会齐心合力共同筑巢。燕子通常是夫妻同回北方,归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先寻找旧巢,如果旧窝还在且能继续居住,它们便衔泥衔草,进行修补,忙碌数日,旧窝修复如新。倘若原先的旧窝不能再用了,它们则立刻构筑新巢。
小时候,我亲眼见过燕子做窝,而且好奇地观察过它们的生活场景。筑巢的燕子起初是一只,后来两只合力。它们从河岸、湖泊、沼泽、水田等水域旁边,衔取湿润的泥土、枯草,再混以唾液,形成小泥丸,然后用嘴从巢的基部逐渐向上堆砌,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外壳,再衔取干的细草茎和草根,用唾液粘铺于巢底,形成干燥而舒适的内垫,再垫以柔软的植物纤维、头发和鸟类的羽毛等柔暖的东西铺就,便可大功告成。它们从始造至结束,大约需要半个月左右。
燕子似乎天生就是勤劳的,一如土地上的庄稼人。“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用一个“啄”字,把燕子忙碌而兴奋的情景写活了,看到它们忙着建造家园,迎接崭新的生活,使人们倍感生命的美好,充满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成年老燕每天早出晚归,日日在田野间,在乡路的上空,飞来飞去,捕捉昆虫,养育后代。它们似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偶尔歇息一下,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一排排栖在电线上,或梳理着羽毛,或呢喃细语,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放大了的省略号。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这首儿歌,村里的大人小孩几乎都会唱。说来也怪,从我父亲到我这两代人,先后在村里搬了三次家。每次迁址,父亲都恋恋不舍地说:“咱们走了,燕子的窝没了,不知它们还能不能找到咱们的新家?”母亲则自信地说:“放心,老马识路,燕子认窝,它们一定会回来的!”新房盖好了,燕子真的飞来了,把窝建在我家房子的屋檐下,长长的屋檐伸出来为它们遮风挡雨,它们住得心安理得。如果哪一年它们不来,或是来迟了,我们心里一定很惆怅。
我家门前的台阶上,经常摆放着两只碗,分别装着小米和清水,每次母亲放好后,就“啾啾”地喊上几嗓子,看到燕子们飞来啄食,她便坐在一旁,欢喜得合不拢嘴。有一次,一只乳燕不知是饿了,还是想学飞翔,不慎从窝里掉落到台阶上,一个劲儿地扑棱着翅膀,老燕子急得不停地尖叫。母亲搬来一架梯子,我手托乳燕,把它轻轻放回巢穴里,老燕立马安静下来,“啾啾”地叫了几声,仿佛是在感谢我们。村子里不光是我家与燕子相处和谐,而且无论新房老宅,燕子总是和村人相陪相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如此感慨,大概也是非常喜欢燕子的缘故吧?


春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