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娟
“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微”正是散步的好时节。傍晚,沿着小区便道漫步,春花虽已辞树,但又见蔷薇初开,月季始艳,小鸟啁啾试着新曲,这良辰美景,怎不令人心生欢喜!
微风拂过,枝叶轻摇,一阵浓郁的花香随风而至,扑鼻的香味,直达肺腑。不是蔷薇、非关月季,这应该是我最熟悉不过的洋槐花的香味。可槐树在哪儿呢?两边的绿化树像列队执勤的士兵,棵棵树干粗壮挺拔,新枝新叶,虽是夜色微澜,也能看见它拇指大的长圆叶片,叶顶尖,正是国槐,北京的市树。远处的主路,这些年逐渐替代成了端庄高贵的银杏树,盼着在秋天,一睹那满天飞舞的金色蝴蝶。我曾是一个匆匆忙忙的赶路人,许久都没有仔细看过一朵花开的样子,所以,记忆中那些不甚高大的、顶着满树白花的洋槐,是何时消失的呢?还是它只存在我的记忆里?
家乡的洋槐树是瘦小的。它比磨盘柿树矮了一大截,树帽也比核桃树小两圈,看着也没枣树结实,树干刚有手腕粗,就着急分杈,细细的枝条上长着椭圆形的绿叶,密密匝匝,叶子里藏着一嘟噜一嘟噜的洋槐花!可花那样白那么香,怎么藏得住!心猿意马终于熬到四点,“铃铃铃”放学啦!书、本、铅笔盒,统统塞进斑驳的木课桌里,缥缈的香味像一阵风似地把我们卷到槐树林里。那是一面向阳的山坡,远远望去,五月的槐花一串串如霜似雪,阵阵甜香令人如醉如痴,蜜蜂嗡嗡嘤嘤上下飞舞,比我们的手脚可要快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洋槐?大概是从国外弄回来的吧。管它呢,白糖似的花儿,又香又甜,早就勾起了肚子里的馋虫,正咕咕叫呢。我们把书包挂在脖子上,捋胳膊挽袖子,男孩子上树,女孩子跳着脚,都要挑一杈花儿多的,掐下一串、一嘟噜,连同甜香的味道一同塞进书包里。“哥,你就顾着吃!”小姑娘叫嚷着树上的男孩,吸了吸鼻子,也将一把槐花塞进嘴里,“真甜!”腮帮子鼓鼓的。是啊,为什么不让咕咕叫的肚子先品尝一下这胜利的果实呢?于是,大家散坐在半山坡上,一边看着血红的夕阳西坠,一边吃着串串白花,家乡的槐花是多么香甜啊。
夕阳渐落,给群山镶了最后一道金边,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大黄“汪汪”地叫唤着我们回家。每个人的肚子都圆圆的,妈妈用布头七拼八凑缝制的书包也都圆滚滚的。一溜儿烟,又都钻回各家的土坯房子里,炉边翻着贴饼子的大姐,追着人影喊:“你没拔猪草?又哪儿疯去了?”我从书包里掏出一串一串的洋槐花,放进黄陶盆里,举到姐姐眼前,她左手拈起一串,右手轻轻一捋,手心里满把槐花,“剁碎了蒸菜团子、蒸窝头都好吃,还可以裹上面糊像炸香椿鱼一样,炸一盘槐花吃,多香!”大姐那样子就像真有一盘香椿鱼摆在眼前!我抚着圆圆的肚子得意地笑了,洋槐花是有用的,我也是有用的!
时光流逝,吃槐花的日子离我越来越远了,后来路边还有了紫穗槐,花儿没有白色的香,艳丽的花朵引来蜂飞蝶舞。再后来,两色的洋槐树都少见了。如今银杏婷婷玉立、国槐华盖森森。那些白色的洋槐花,如同这微醺的五月,只有一缕暗香可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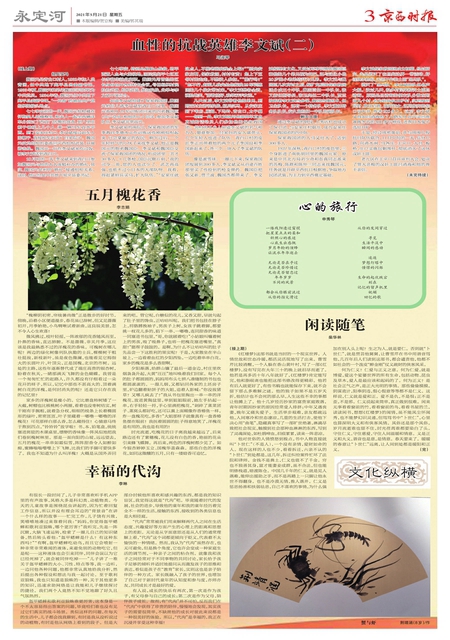
五月槐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