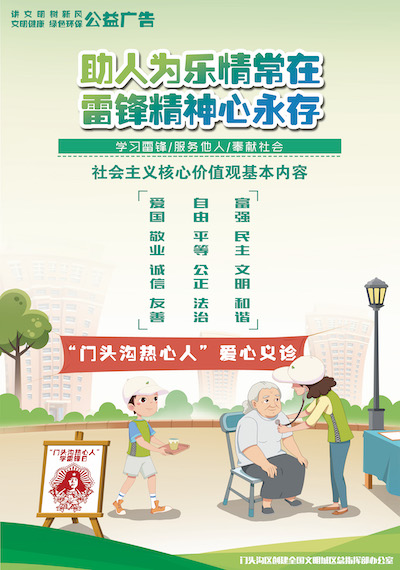张新民
夏至将至,骄阳似火。在电视里看到由绿转黄的麦田忽然感觉到,麦收时节又到了。金黄色的麦子是农民的希望。在一片金黄的光晕里,有我青春的记忆,更有我在热辣辣的阳光下,抢收夺麦时流血流汗的回忆。这种刀耕火种般的农活儿真的让人刻骨铭心。那个年代,农村主要从事粮食生产,种植的品种主要是小麦、玉米、谷子,白薯等。我家住在京西永定河畔,属于京郊浅山区,这里没有成片的麦田,面积大的十几亩,小得只有几分地。当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效率却比较低,一个麦季少说也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
麦收时节的记忆,首先想到的是紧张和忙碌,伴随着无奈的汗水和迷茫的企盼。在我的家乡,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三夏大忙,宁掉十斤肉,不丢一粒粮。”怎么会把正常的夏种夏收割麦子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呢?可见当时的三夏农活儿苦得沉痛、苦得深刻。村里人多地少,麦收时节完全靠人工收割、人工打场。并且常常要与突如其来的阵雨争时间,抢速度。所以麦收时节最常听到的口号就是“龙口夺粮”。
三夏开始了,社员们不分昼夜,抢收割、抢脱粒、抢播种,生产队长带头冲锋在前。记得那年我只有十五六岁,凌晨三四点钟,就和社员们来到了地头,队长先是让记工员清点人数,然后点上一袋“地头烟”,随后第一个弯腰割麦。我置身于清晨空旷的田野里,和社员们一起一字排开,紧张地挥舞着镰刀,只听见镰刀嚓嚓响,麦子一片片倒下,接着低头捆麦,再弓腰收割,眼见着随风摇摆的麦穗变成了一个个麦捆儿。队长再三叮嘱我留神麦垄之间的玉米苗,小心不要和麦子一起被割掉。我努力地弯腰躬背,挥镰割麦,不一会儿全身汗如雨下,衣衫浸透。八九点钟的时候,太阳高高地爬上了头顶,热辣辣的阳光照在身上,像一团火包在身体周围,这个时候一般上午割麦任务就基本结束了,稍事休息,喝点水、吃点带来的干粮,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装车把麦子运到打麦场。装车是最遭罪的事,割倒的麦子经过阳光的照射,露水已经没有了,一根根麦芒就像一根根钢针长在麦穗上,麦穗上的尘土也都飞扬起来,麦子一捆一捆地装到马车上,车越装越高,装车也就越来越困难,需要一个人站到车上接车下的人扔上来的麦捆,最后用大绳和搅杠把整车麦子刹结实,运到场院去。装车时麦芒扎得浑身痒痒的,身上到处是一片片的小红疙瘩,胳膊上有,腿上有,脖子上也有,吸进嘴里和鼻孔里的都是麦子上的尘土,吐一口痰都是黑的。这种没白没黑的劳作,真是累得我们人困马乏,叫苦不迭。
年过半百的老队长跛着腿总是在人们快要崩溃的前半晌和身体即将放(虚脱)了的后半晌,及时地派人挑来两大桶绿豆汤。这微微发红的绿豆汤,不仅让我们消暑解渴,更能让我们在苦不堪言的状态下得到一丝慰藉。同时也能让我们躲开炎炎烈日,到树荫下稍微歇息一会儿。生产队里的壮劳力们,白天趁着天气晴朗抢收麦子,晚上还要浇灌收完麦子之后略显干旱的玉米地,第二天又要赶到打麦场给小麦脱粒。只有在下雨时,,或者扬场等风时才能躲在麦垛后的空隙里,或者树荫下躺一躺,展展腰、松松胯,算是休息。在这样一个时间比较长的麦收季节,对一个男劳力来说,真是能让人掉几斤肉,脱几层皮,难怪会有那样的口号。
有句农谚叫“忙不忙,看打场。”这是很有道理的。麦收期间打场脱粒最怕遇上阴雨天气,刚脱出的麦粒,如果遇上雨天,可以分到社员家里摊在屋地下,或者晾在炕头上,怎么着都好办。如果麦穗还未脱粒,淋雨后在场院堆着,麦粒就会发芽、发霉,到嘴边的粮食就吃不着了。因此人们把打场看得格外重要。打场这活儿,说是比割麦轻快儿些,其实也轻快不到哪里去。“文革”前,我们村还没有脱粒机,当时,人们将割回来的麦子在打麦场上摊开,铺成巨大圆形,套上大牲畜,拉上石轱辘一圈一圈地在铺开的麦秸秆上走,碾场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无聊。辛苦是因为碾场需要在阳光最毒的时候顶着烈日进行,无聊是要赶着牲畜在原地不停地转圆圈。有经验的老农,会看着前面牲畜的动作。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拿着鞭子。甩的鞭子啪啪作响,如果牲口出现大便还要及时清除。碾场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翻场,实际上就是将已碾过的铺在上面的一层麦秆翻到下面去,将下面没碾到的翻上来,反复碾压,反复太阳晒。到了下午大约三四点开始起场,大家用木杈将已经脱粒的麦秸挑开,挑到一侧。留在原地的麦粒和叶子一起攒堆,准备扬场。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场院打场,太阳热烘烘的,但微风习习,送来几丝凉爽。老队长歇也不歇地扬着麦粒,旁人铲进簸箕一锨,他就要侧着风扬出一锨,我和两个社员拿着竹扫帚,把扬出的麦粒和麦壳渐渐分离出来。扫帚要轻轻地扫,浮在上面的是麦壳,下面的是麦粒。如此重复不休地动作,使麦粒形成一堆。麦壳扫到一处,再把场上的麦秸,整个用杈抖一遍,拢成堆,垛成麦秸垛。麦秸垛垛好后,还要从外表上进行修葺,即用木钗挑去垛四周上多余的麦秸,使其看上去更紧凑,更整齐。顶上放一层麦鱼子(麦壳),这样,下点小雨不会往下渗。接下来老队长还要用木钗穿进垛子的边底,用力往上撩,我们把垛下残留的麦粒清扫出来,这样一钗钗撩过去,把整垛麦秸都掏扫干净了,虽然扫出的麦粒并不多,但是这是麦收打场的必要程序。
“文革”期间,村里有了脱粒机,打场脱粒的效率提高了,场面也更热闹了,机器轰鸣,尘土飞扬。为龙口夺粮,麦田和麦场形成了两个战场,一边是抓紧收割,将收割的麦子运往麦场,一边是麦场的人们轮番作业,一台电动脱麦机通宵达旦地运转。人歇马不歇,搞得村里深夜脱粒机轰鸣不断。脱麦机打场是个又累又脏的活儿。要有八九个人共同作业,才能完成工序。男社员光着脊梁,女社员头戴草帽或围上头巾,他们把麦捆打开,扔到脱粒机平台上,机上的人用手均匀地把麦杆“喂”给脱粒机,,吐出来的是麦粒和麦秸。麦粒归到一堆,麦秸挑到远处垛起来。,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见到了,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劳动场面!我的二叔从生产队买进脱粒机开始,就是队长重点培养的脱粒手。记得那一年是1970年的麦秋,二叔站在脱粒机上忙活。由于他连日劳累,体力不支,再加上当时是个夜晚,他不慎把右手连同麦杆一起裹进了脱粒机里。只听得一声惨叫,接着就从站台上滚了下来。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等几个壮劳力从惊慌中清醒,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了运麦的手扶拖拉机上,连夜送到区医院。二叔做了手术,把小腹的皮殖到手背上右手才保住。如今,每每回想起这些,我还是心有余悸,毛骨悚然。
40多年前的麦收时节,倾注了我太多的青春岁月。那金黄的麦浪,烈日下的镰刀,黝黑的脊梁,场院的轰鸣声,还有那杏树底下掉下的一层熟透的香白杏。这一切,对我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那种对土地与收获的期盼,以及麦收期间因天气变化产生的那份揪心的牵挂,都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如今很多记忆已逐渐淡忘,打谷场与石磙已不复存在。但麦收时节的一些往事,却时常萦绕于心怀,如梦似歌,牵动着我对早已逝去的青春的怀念。怀念三夏战场上的劳动场景。


- 标题导航
- 北京首例自考替考案开庭
- 我区专项检查集期市场生鲜肉
- 飙车致人受伤,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 两人打架伤及第三人责任应如何划分?
- 区工商分局开展虚假广告查处工作
- 永定暑期安全法治课开讲
- 区城管局联合整治城乡结合部环境秩序
- 房屋漏水不是小事 各方携手方能解决问题
- 门头沟区2016年夏秋季征兵公告
- 如何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
- 大峪中学西校区开展游学活动
- 京煤总医院被授予中华精准健康传播基地
- 区质监局特检所通过锅炉能效测试能力验证
- 区质监局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
- 代码窗口转变工作方式简化服务流程
麦收时节